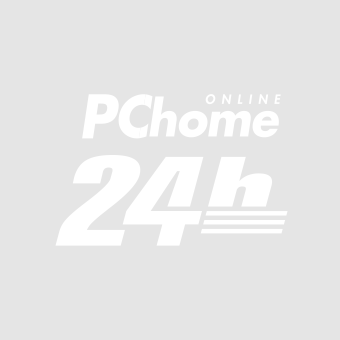商品詳情
內文簡介
- <內容簡介> 從吳念真到蔡明亮,本書擺脫無聊的修辭與公式,徹底鍛造你的寫作鍊金術! 寫作有方法嗎?故事為什麼重要? 本書並非傳統的作文書,既沒有目光如豆的修辭,也沒有食古不化的公式,而是透過貼近創作名人的生命史、成長史,將書寫、閱讀以及個人經驗作一參照,透過二十位老中青三代的知名創作者,闡述創作的核心命題、自我鍛造與困境。引領讀者從中獲知寫作的想法、做法乃至心法,對於提升中學生乃至大學生的寫作力深具助益。 全書共分四輯,輯一「父親,最最遙遠的距離」、輯二「翻滾吧!夢想」、輯三「越健康越空虛」,共訪談吳念真、詹宏志、蔡明亮等不同世代的創作者,由其現身說法,如何面對創作的甘苦談。輯四「故事創意與方法」,則由本書作者加以歸納,說明「何謂故事」、「如何講故事」、「該講什麼故事」,引領讀者實踐故事、實踐創意,並且面向自我。 寫起來吧,故事力! ★專家推薦: 《明道文藝》創社社長 陳憲仁 吳三連文學獎散文獎得主 林文義 政大廣告系兼X實驗學院籌備處教授 陳文玲 師範大學臺文系副教授、國際臺灣研究中心副主任 莊佳穎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時間你慢慢的走》作者 蕭義玲 ★目錄: 輯一 父親,最最遙遠的距離 1.父親,最最遙遠的人間條件 最最念真情的「歐吉桑」 吳念真 2.在奔赴流光前塵的路上 捕捉記憶與真實者 詹宏志 3.電影不是我的夢想 永遠的漂泊者 蔡明亮 4.迷路的詩,迷宮的小說 博學的點石成金者 楊照 5.以減法以理智面對小說 原鄉的追索者 瓦歷斯.諾幹 6.我又恢復成人了 小說鍊金術師 大江健三郎 輯二 翻滾吧!夢想 7.我最好的作品尚未出手 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 黃凡 8.如何獲得自由 跨國際與跨文化的思索者 平路 9.惦記著那些在他們身世裡的自己 說夢人 駱以軍 10.特別不同是頂困難的事 大智若愚者 劉震雲 11.寫自己的小說 冷眼的秀異的獨行俠 郭箏 12.翻滾吧!夢想 無限可能的翻滾 林育賢 輯三 越健康越空虛 13.誰來隱喻 疾病與身體的關注者 李欣倫 14.運詩人就是我 沉靜的慧黠的閱讀者 房慧真 15.一直在虛耗 真誠的虛構者 龔萬輝 16.一生只過一種生活 暴烈的疏離者 黃宜君 17.虛構的謎中之謎 本質性小說家 童偉格 18.我就是想開一家書店 不甘心過這樣的日子 686、隱匿 19.再刺激一點,再刺激一點 小說詩人 馮瑀珊 20.他媽的。我什麼都不能做 鋼鐵詩人 洪書勤 輯四 故事創意與方法 21.故事定律一:永遠不要小看故事 尋找唐先生,尋找獨家故事 22.故事定律二:故事總是包含了「看世界」的觀點 我的前世是一隻海豚…… 23.故事定律三:永遠別忘了你的讀者與目的 兔子啟示錄 24.故事實戰一:建構強大的心靈景觀 我就是喜歡走在修羅之路上! 25.故事實戰二:出發尋找靈感 假如姐姐是JJ 26.故事實戰三:打造三幕劇 當他醒來的時候,恐龍還在那裡…… 27.故事實戰四:進入主角的身分 小資女孩.高級景觀餐廳.愛 28.故事實戰五:驚典錄的必要性 未來的海賊王夥伴,不要露出那種沒有出息的表情 29.故事絕招一:物的變形記 卡夫卡與孤獨三部曲 30.故事絕招二:新聞化小說 馬奎斯與自己出生當天的事 31.故事絕招三:二元並置 村上春樹與《海角七號》 32.故事絕招四:絕對要比文學獎大 文學獎攻略面面觀 跋 用一個故事來換 <作者簡介> 張耀仁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博士。 現任國立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文學作品曾獲《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等,曾入選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並曾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學類創作及出版補助。 學術著作曾獲國立臺灣文學館傑出博士論文獎,國立屏東大學110年度研究績優教師獎,112年度優良導師獎。 著有: 短篇小說集:《親愛練習》、《死亡練習》、《讓我看看妳的床》等 散文集:《最美的,最美的》、《愛根本瘋狂》 作文書:《會考作文滿級分》 素養書:《網紅‧假新聞‧偽科學:媒體素養必須知道的20 堂課》等 圖文書:《喵!記得明天依然愛》 學術書:《臺灣報導文學傳播論:從「人間副刊」到《人間》雜誌》 ★內文試閱: 父親,最最遙遠的人間條件 最最念真情的「歐吉桑」吳念真 吳念真(一九五二~),本名吳文欽,生於九份,父親是來自台灣嘉義民雄的礦工。一九七六年考入輔仁大學夜間部,主修會計。一九七六年起從事小說創作,多以中下階層為對象,曾獲聯合報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著有短篇小說集《抓住一個春天》、《特別的一天》等。一九七八年起從事電影劇本創作迄今,多部台灣新電影劇本皆出自其手,並執導電影《多桑》、《太平天國》。九○年代起主持電視節目《台灣念真情》,並於電視廣告大量曝光,成為台灣炙手可熱的媒體人,現為自由編劇。 所以,吳念真再次提起了父親。 提起父親的時候,吳念真還是忍不住從父親十六歲北上九份挖礦說起,還是忍不住談到父親戲劇性的成為別人的兒子(他說:「我爸是嘉義民雄人,和後母吵架跑到九份,看到有一對夫妻死了兒子,就說『你們不要哭,我給你們當兒子』,就這樣成了人家的後生……」),又因為人家希望兒子常在身邊,所以招贅成為女婿,也是父親姓連,吳念真之所以姓吳的緣故(他說:「我爸這輩子最怨嘆的就是他最得意的後生,卻與他不同姓……」)——這個習慣自稱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出生的父親,十七歲前接受的恰是後來被國民政府稱之為「奴化」的日本教育,一夕之間,台灣「光復」了,禁用日語也禁唱日文歌曲 ,原本自信的父親頓時變成了「文化孤兒」,「所有他接觸的東西,和他過去所受的教育都是牴觸的。」吳念真說。 這樣被時代拋棄的父親,淪為不懂得表達情感、「失語」的台灣男性,「從來沒有和小孩有什麼親密行為,一如日本人不擅於訴說心緒,就是酷在那裡,也不知在酷個什麼勁?」吳念真低喃,年輕時很怕父親,「只要一個眼神,就足以把你嚇死,巴不得他天天不在家!」然而,某次陪父親至村裡極其偏僻的山神廟拜拜時,一個等待燒金紙的空檔,父親突然自言自語道:「我這世人,不輸鳥仔飛入籠欸。」意思是,命運半點不由己,青春無彩。 許多年後,吳念真也為人夫、人父,這才逐漸懂得父親當年之壓抑、之無可奈何,「畢竟我也是很壓抑的人,常常把許多事情往肚裡吞,但我承認這是『不健康』的。」吳念真又說了許多許多,多半是東湊一點、西拼一塊的父親之種種。事實上,這些零散的片段早在一九九四年執導的電影《多桑》,便已組合成「想像中的父親」。但他依舊不厭其煩的再次提起這些,彷彿隔了一整面毛玻璃怎麼看也看不真切的,那是距離最最迢遠卻始終召喚著生命的源頭的,關於父親的一切。 關於不知從何溝通的那個原點。 ● 就在狂風暴雨中,多桑竟告訴我說,因為他招贅,兒子才姓吳,要我千萬記住,我是「吳皮連骨」,以後「找查某,不能找姓連的,周都不要,因為『蘇周連』是一家。」還問我知不知道差點被他溺死在水缸的小弟為什麼叫「嘉民」,他說,這樣,你們永遠就不會忘記,你們的故鄉是在嘉義縣民雄鄉(吳念真,《多桑:吳念真電影劇本》) ● 所以,二○○一年吳念真跨界編導第一齣舞台劇《人間條件》(後稱《人間條件1》),即著墨於「溝通之可能」、「瞭解之可能」。 不同以往,這次壓抑的父親形象變成了聒噪不已的里長伯兼六合彩組頭。在這齣十一月下旬(按:二○○八年)重新開演的《人間條件1》中,由李永豐飾演的里長伯熱心服務里民,卻不懂得如何面對青春期女兒,加諸整天沉溺於電視的自閉老婆,等於是一部檢視「家庭內部」、「家庭壞毀」的親情劇。劇中的女兒阿美這麼說道:「阿媽,我跟妳說真的,我在家裡的時候不想上學,放學的時候不想回家,有時候坐車或走路的時候,我都會想說:我在做什麼,從不快樂的地方又要到另外一個不快樂的地方……」 吳念真說,他期望透過戲劇與觀眾互動、達到情感上的交流,「我們能不能讓一輩子從未看過舞台劇的人進來?讓他們覺得親切?能不能不要那麼難懂?」比方在《人間條件2》裡,有一個片段是二二八事件後,國軍強行進入民宅搜索,臨走前訓斥居民「要不是我們八年奮戰,哪來台灣光復?你們還不知足、不感恩?」當場有一位老先生就在後排喊:「我聽你在放屁!」 凡此種種(觀眾間流淚時互相傳遞衛生紙、演員好心提醒觀眾快去接手機等等),在《人間條件》系列上演過程中,皆成為該劇的一大特色。為此,吳念真極其感動,認為此劇實踐了他當初下筆時的心情:讓觀眾從中看見「溝通」。他說,在編導《人間條件1》之前,不懂得舞台劇章法,也從未涉足舞台劇,但他以為當代台灣媒體的通病,在於人與人之間未能真正溝通,「即使有,也是從自身的觀點去解讀,而非站在對方的立場看事情,所以很多媒體報導反而加深了彼此的『誤解』。」 他提及新婚時,太太一不高興就繃著臉、什麼也不肯說,「但我猜不到啊!」吳念真苦笑著,「後來我就告訴她:對我有什麼不滿可以說出來,如果說不出來可以用寫的。」多年來,他和人相處總是「坦誠相見」、「把心門打開」,他以為人與人的相聚即是緣份,「如果相識一場,轉身離開卻變成陌生人,那又何必當初?」因而《人間條件1》,即藉由逝世多年的老阿媽附身於孫女上,將某些埋怨說出來,同時也揭露了父女、夫妻間,一直以來不被理解之處,一如女兒阿美說:「阿媽,你回來真的很好欸!讓我知道爸爸很多故事,也知道他很愛我們、很照顧我們。我只是不懂,人為什麼要隱藏自己呢?如果不隱藏,人與人之間不就更容易接近嗎?」 也因為父親的壓抑與棄絕溝通,使得吳念真將兒子當作朋友看待。「我常常跟我老婆講,要相信兒子是獨立個體,擁有獨立選擇的能力。」他以自己為例,十六歲即外出半工半讀,從未有家人在旁督促,「還不是這樣活過來了?也選擇了一個自己滿喜歡的工作啊。」吳念真以為,當代父母的責任即是陪伴孩子度過每一個人生關口,讓他們在徬徨時有所依靠,「我說,如果我兒子失戀能夠向我傾訴、甚至哭泣,那我這輩子真的就不虛此行了,因為兒子是如此、如此的信任我啊。」 說這些話的吳念真,讓人再次想起《多桑》裡的一幕:兒子送飯給剛從礦坑裡出來的父親,父親吃完飯後躺在棚下小憩,這時候,雨落下來了,兒子抓了塊塑膠布遮住父親受傷的腿,任憑雨水打在自己的背上,深怕西北雨驚醒父親——那樣雨中幽微的即景,屬於父子最最深層的情意,卻始終不發一語,沉默,沉默。 ● 阿媽說:「這世人,有一半,是因為有你,我才感覺有意義,有幸福。未來的歲月,我看你不著,但是,拜託你,千萬要平安,千萬要幸福,拜託你。」(吳念真,《人間條件1》) ● 所以,除了劇本,除了電影,曾經獲得聯合報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的吳念真,當真不再寫小說了嗎? 對此,吳念真嘆了口氣:「也許等老一點吧?畢竟小說還是滿好玩的。」他意有所指道:「小說的成本最低啊。」惹得在場所有人一陣大笑,因為在這句話之前,吳念真剛談到這些年來從事編劇的頹喪心情:沒有堅實的政治實體,更沒有文化作後盾,電影淪為台灣(甚至是好萊塢以外)的奢侈品。在票房慘跌的情況下,他既不願虧欠出資老闆(「那是一輩子的愧疚耶,因為錢不好賺啊。」他說),也不願違背自己的心意(「二○○七年幫公視拍了一部《哪裡有光》,是關於原住民的議題,花了五六百萬,後來由於一些特殊因素沒情感了,我寧願跟對方說我不拍了,錢還你。」他說),因而一九九六年拍完《太平天國》後,吳念真即停頓了執導工作。 也正是當年轉行從事編劇的緣故,吳念真在面對題材時,總會想著:「這可以拍啊。」他以為閱讀小說需要一些「才能」:比方想像力、聯想力、還要有文學素養,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具備這樣的能力,例如礦工未必閱讀礦工小說,「等於他們沒有被安慰到,因此我寧願用影像去說,它最直接。」吳念真表示,近年來國內年輕作者的作品「太空泛」了,「好比『一粒田螺打九碗湯』 ,明明是一件小事卻寫了六七千字、甚至幾萬字!」他喜好的是黃春明或陳映真之類的作品,「能夠以情感結結實實的打動我。」 對於多年來從事的劇本與小說創作,他笑說兩者「都不及格」,尤其面對大師級作家的年表,「看看人家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就寫出那麼好的東西,而我呢?頭殼裝屎嘛。」經常心虛的結果,使得他很少留東西,「寫完就算了,什麼都不留,就連當初出版小說也是出版社自行找來稿子的。」他說,自己最好的作品還未出現,「否則人怎麼活?如果最好的東西出現,那不就可以去死了嗎?可以得貢獻獎了嘛。」 鬨堂大笑中,吳念真同樣露齒開懷,眼角卻浮現難以遮掩的抑鬱,那或許是相對於整個媒體環境的憂畏,「不要只看到它表面的繁華,也要看到其中無人知曉的寂寥與折磨。」他這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