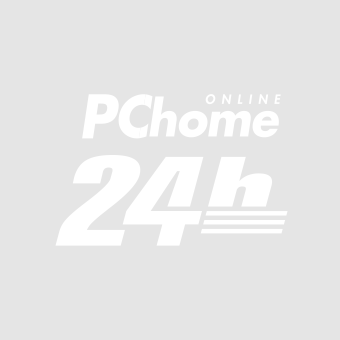商品詳情
內文簡介
<內容簡介>
◆日本神道文化體驗者、最理解大和魂的西方人◆
——小 泉 八 雲——
十四篇記錄民俗與傳說、人性與玄怪的奇情短文
細膩捕捉日本文化中質樸深幽的陰翳之美
===================
▋命運多舛,卻成就小泉八雲不平凡的一生
在日本文學史上,一旦說起妖怪文學,小泉八雲毋庸置疑是此文類的鼻祖;而在日本近代史上,小泉八雲更是將日本文學推向世界潮流的第一人,被稱為是最理解大和魂的西方第一人!
原為希臘人的小泉八雲,由於童年顛沛流離的生活所致,養成其敏銳的觀察力與感性多思的共情能力。在他初次接觸日本文化後,便對這異國風情心生嚮往,自此投身日本文化與文學的研究、翻譯與創作領域中。
小泉八雲與日本的連結,除了在於他翻譯不輟、為西方打開一窺日本文化的窗扉,自己更與日本女子小泉節子婚娶,歸化日本籍,就連日本名八雲也出自最古老的書籍《古事紀》中的歌謠「八雲立,出雲八重垣」。
▋以細膩文采紀錄民俗傳說,幽微展現人性的真面目
小泉八雲透過西方人的視角,以獨到的觀察力將日本文化中幽微隱密的部分抽絲剝繭,成為日後人稱妖怪文學的濫觴。也有人說在小泉八雲筆下的民俗傳說恰如日本版的《聊齋》,以玄怪的包裝訴說人性真實面。
而在《幽冥》一書中,小泉八雲便以十四篇充滿怪誕奇想的短文,揭露日本人內心深層最為陰暗、恐懼、甚至是自私的那一面。這些短文全是小泉八雲所整理,關於民俗傳說、鄉里見聞的深夜奇談,呈現一個西方人對日本傳統、故事、文化及信仰的獨特觀察。
脫胎自日本三大怪談的〈牡丹燈籠〉,以女子對情人至死不渝的愛慕為基底,形式上將燈籠與鬼魂、祭祀信仰的概念結合,訴說因果報應的故事,發人深省;此外,〈因果話〉傳達欲望與嗔念的極致恐懼並非肉體殞滅便能了結;〈嗚嚎〉更以耳聞犬獸之聲的探究,進入討論生命哲理與精神信仰的層次;最後在〈燒津〉一篇結合盂蘭盆節的地方風俗、羽島娘的鄉里傳說與追水燈的個人體驗,將一個西方人對東方文化的觀察描寫得絲絲入扣,盡顯日本文化中質樸深幽的陰翳之美。
如同小泉八雲在〈碎片〉一文中所提:「我們爬的永遠是自我心靈的山,害怕、恐懼的惡魔不過也是自我顯現的一部分。」本書所寫的鬼神信仰、傳說見聞,更大程度是體現大和民族面對無法言說、對未知事物的真實感受,其中穿插了宗教與民族性的演示,在在傳遞這個民族所具備的精神哲思。
★目錄:
【 壹 】_碎片
【 貳 】_振袖
【 參 】_焚香
【 肆 】_占卜
【 伍 】_蠶
【 陸 】_牡丹燈籠
【 柒 】_佛足印
【 捌 】_嗚嚎
【 玖 】_短歌
【 拾 】_與佛教有關的日本諺語
【拾壹】_暗示
【拾貳】_因果話
【拾參】_天狗話
【拾肆】_燒津
<作者簡介>
小泉八雲(1850-1904)
曾任新聞記者、旅行作家,後因定居日本,開始從事日本文化與文學翻譯,並從事創作。小泉八雲原名拉夫卡迪奧.赫恩(Lafcadio Hearn),出生於希臘的愛奧尼亞群島,父親為英國派駐當地的愛爾蘭軍官,母親則是希臘人。
赫恩的童年生活坎坷多舛,他在出生後不久,一家人便遷回父親故鄉愛爾蘭,但母親因故備受夫家親族冷落,加上夫妻聚少離多,便在赫恩七歲時獨自搬回希臘。赫恩的父母後來解除婚約,各自重組家庭,赫恩便交由親戚收養,進入教會學校就讀。無奈撫養他的親戚在他十七歲時破產,自此赫恩便轉往倫敦投宿在親戚的僕人家,開始了顛沛流離的青少年生活。
赫恩十九歲時在親戚的幫助下,以一張單程船票踏上前往美國紐約的旅程。一貧如洗的赫恩最初只能在低階的工作中打滾,後來憑藉優異的文學素養進入報社工作,開始發表翻譯與著作。成年後的赫恩因工作調派關係,曾前往歐洲及美洲各地採訪寫作,四十歲時受《哈潑》雜誌派往日本採訪,自此與日本結上不解之緣,陸續在松江、熊本和神戶生活,最後選擇落腳東京。
曾任記者的赫恩精通多種語言,擅於觀察,且熟諳東西文化。對迥異於西方的日本風土及文化甚為喜愛,因此於四十六歲(一八九六年)歸化日本籍,同時冠妻姓,改名小泉八雲,並於東京帝國大學任教。由於十九世紀末的西方大眾對日本所知不深,他以英文撰寫關於日本文化的多部著作,扮演起西方世界認識日本文化的重要橋梁,被稱為最了解大和魂的西方第一人。
譯者:蔡旻峻
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藝術管理研究所畢業,曾任職出版通路、雜誌企劃、書籍企劃、翻譯與編輯。
★內文試閱:
試閱(一):〈燒津〉
一、
耀眼陽光下的老漁村燒津,有著灰色的獨特魅力。它沿著小小海灣,宛如蜥蜴般地與座落所在的原始海岸的淡灰色融成一體。這座水畔堡壘是以層層階台的樣式建成,幾排深深打進地裡的樁柱架起類似籃網編織的網子,固定住顆顆卵石;幾列個別的樁柱撐起每層平台。從台階最上層望向陸地,全村盡收眼底。那是一片灰色屋瓦和歷經日曬雨淋的灰色木料構成的廣闊空間,散落各處的松林則標誌出寺院所在。至於另一頭的海景,一大片水面上是一幅浩瀚景象。水平線上群聚著層峰交疊的藍色山巒,宛如巨大的紫水晶,群山之後的左方是壯觀高聳的富士山,睥睨萬物。防波堤和海面之間不見沙灘,只有一道多為卵石的石堆積聚成的灰色斜坡。這些卵石隨浪翻滾,要度過狂風暴雨之日拍打上來的浪濤並非易事。如果你曾經困在石浪中,這我就曾遇過幾次,那經驗絕對難以忘懷。
某些時分,這崎嶇不平的斜坡上有一大片會擠滿數列造型獨特的船隻,那是當地漁船獨有的造型。這些船相當大,每艘都可容納四十至五十人,船頭更是異常地高聳,上頭通常繫有佛教或神道教的咒文(御守或守護)。船頭常見的神道教咒文正來自富士女神神社,上頭的文字為「富士山頂上宣言具大魚滿足」,意即若是能滿載漁獲而歸,船主發誓會齋戒苦行,以表達對富士山頂那神靈的敬意。
在日本靠海的各省、甚至同省的不同漁村內,漁船和漁具都有獨屬當地的特殊樣式。有時確實會發現,相距不過數哩的漁村,彼此各自作成的漁網或漁船,形式差異之大,竟像是相隔數千哩的民族所發明。某種程度上,這令人訝異的多樣性或許是源於村民對當地傳統的崇敬,是對保留祖傳數百年教導和習俗的虔誠保守主義的尊敬。
但更好的解釋是不同的漁村會有不同的捕魚方式,各地的漁網或漁船樣式,都可能是當地按特殊經驗研究過後的發明。燒津當地的大船便說明了這一點。這些大船是根據燒津當地的漁業需求、也就是供應柴魚至日本帝國各地所設計,因此必須適合在波濤異常洶湧的海面航行。要讓大船入水或上岸非常難,不過全村的人會一起幫忙。有一種下水滑道是臨時在斜坡鋪上一排平坦的木頭,然後將底部扁平的船放在木頭上,藉由長繩索朝上或往下移動。你會看到上百位民眾一起拉動一艘船,男女老少同心齊力,唱和著一首奇特的憂鬱曲調。颱風來臨前,村民會將船隻從港口移往村內街上。幫忙這種事有許多樂趣,而且如果你是個外地人,漁人或許會拿出海中珍鮮做為辛勤之後的報酬:長度驚人的蟹腳、誇張地脹成氣球的河豚,以及各種樣貌奇異的海鮮;你還沒動手摸看看之前,幾乎不會相信這些竟是自然界的生物。
船頭貼上咒文的大船還不是海邊最奇特的東西,更特別的是竹片編成的餌籠。這些圓鐘型的籠子高六尺,直徑八尺,頂上還有一個小洞。從遠處看,在防波堤上並排曬乾的餌籠可能會被誤認成是某種住所或小屋。接著你會看到一座巨大的木錨,樣子像個犁頭,上頭還鑲有金屬;還有四個鈎腳的鐵錨,打樁用的大木槌,以及各種陌生的器具,你甚至猜想不到它們的用途。這些難以形容的古怪老東西,會讓你感受到奇異的遙遠感,像是身處迢遙時空,讓人懷疑起眼前所見的真實性。燒津的生活確實也維持著數百年前的樣貌。燒津人就像古代日本人,直率一如赤子,勇於認錯,對外界一竅不通,而且虔誠尊崇古老傳統及神明。
二、
燒津正值盂蘭盆節的三日祭典那時,我人剛好在當地,因此希望能在第三天、也就是祭典終日,瞧瞧那美麗的送別儀式。日本許多地方都會以小船安置魂魄,讓幽魂能乘船上路,這些船多是帆船或漁船的縮小版。每艘小船都裝載著供品、清水和焚香;如果這幽魂之船是在夜間出發,還會附上小燈籠或油燈。不過在燒津,只有燈籠單獨漂浮在海面上,而且據說燈籠只在天黑之後下水。別處慣例上是在午夜時分送別,我推測在燒津亦然,因此我在晚餐過後還偷懶地小睡片刻,希望能準時醒來觀賞送別燈籠的景象。但當我夜裡十點又來到海邊時,祭典早已結束,人潮也已返家。這時我看到海面上猶似一長群螢火蟲的東西,那是正漂流出海的燈籠,但它們已經漂遠到只能從點點燈色辨認。我很失望,因為自己的貪睡,竟錯過或許再難相遇的機會,因為這些古老的盆節習俗正疾速消逝。但我突然同時想到,我可以冒險游過去跟上那些燈火,因為它們漂得很慢。於是我脫下袍子留在岸邊,跳入海中。海面相當平靜,而且散發著美麗的燐光。我的手每划動一次,就會揚起一道黃色火光。我游得很快,比我預期的快上許多,就游到了燈籠群的尾巴。但我想若是出手阻擾這些燈籠、或者讓它們偏離安穩的航道並非合宜之舉;於是心滿意足地緊跟著其中一盞,研究起燈籠的細節。
燈籠的結構相當簡單。底部是一片十分方正的厚木板,長約十吋。燈籠的每一角都有一根高約六尺的細條支撐,而這四根豎直的長條則藉由四張紙在頂上交會。燈籠中間有一根直立在木板中心的長釘,固定住一根燃火的蠟燭。燈籠上頭是開放的,四邊則繪上藍、黃、紅、白、黑五色。這五色分別象徵空、風、火、水、地,在抽象上亦與五佛一致的五種佛教元素。其中一張紙壁繪上了紅色,一張為藍,另一張為黃,第四張紙壁右半為黑,左半邊則未繪上任何顏色,以代表白色。透光的紙壁沒有寫上任何戒名,燈籠中只有火光閃爍的蠟燭。
我看著那些脆弱的發光體漂過黑夜,它們散落四方,彼此隨著風浪起伏越離越遠。每盞微微震顫的光點都像是一個懼怕的生命,在載著它們漂向遠方黑暗的盲流中搖曳……我們難道不也是一具具漂向更黑更深的汪洋,因為難免的離散,彼此終將漸行漸遠的燈籠?思想的燭火轉瞬就將燃燒殆盡,脆弱的燈籠和曾經美麗的色彩隨後就將永遠溶進那無色的「空」。
即使在這沉思時分,我卻懷疑起自己此時是否真是獨自一人,自問身邊除了搖晃的閃爍燈火之外,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東西:某種糾纏在漸逝火光旁、正看著我的東西。一股寒顫瞬間襲來,也許是打從心底升起的哆嗦,也或許只是因靈異念頭而起的毛骨悚然。我想起一則古老的海邊迷信,依稀是「亡魂遊走時相當危險」的古老警告。我心想,要是我在這夜裡因為妨礙亡者之光、或是看似有意妨礙亡者之光而遭逢邪靈,那麼我可能會成為未來某個詭異傳說的主角……於是我對著燭火默唸超渡的佛經,趕緊遊返岸邊。
當我摸到岸上礁石時,卻因為撞見眼前兩道白影,嚇了一跳,但聽到親切的聲音問我海水是否會冷,我便放了心。原來那是我的老房東漁夫乙吉。他剛好和妻子來找我。
「是很舒服的冷。」我披上袍子跟他們一同返家。
「啊,這樣啊,」房東之妻說道。「盆節之夜外出不是好事喔!」
「我沒走遠,只是想看看燈籠。」
「就算河童有時也會溺水,」乙吉大聲說著,「村裡以前有個人因為船沉了,他在狂風暴雨裡游了七里想游上岸,最後還是溺死了。」
七里大約只比十八英里短一點。我接著問,現在村裡的年輕人有人能游這麼遠嗎。
「有幾個也許可以,」老房東回答,「這村子有很多游泳好手,大家都在這裡游,連小孩子也是。不過,漁夫為了活命才會游這麼遠。」
「或者談戀愛時,」房東之妻補充,「就像羽島娘那樣。」
「羽島娘?」我疑惑地問道。
「某個漁夫的女兒,」乙吉說道,「這女孩曾有個戀人名叫網代,兩人相隔七里遠;她常在晚上游過去找他,在清晨時游回來。網代都會燃火為她指引方向。但某個暗夜裡,他忘了點火,也或許是火把滅了。她在海中失去方向,最後溺水身亡……這個故事在伊豆相當有名。」
「那麼,」我自問,「在東方,英雄會游泳是相當可悲的事。在這種情況下,西方人又會怎麼評價希臘傳說中的利安德?」
三、
通常盂蘭盆節的時刻,海面都會開始變得洶湧;隔天早上看到風浪變大,我其實不太訝異。這風浪會持續整天。這片波濤在午後顯得十分壯麗,我坐在防波堤上觀賞這片景象,直到日落。
那浪濤捲得悠長又緩慢,巨大且駭人。有時就在浪碎之前,綠色的長浪會發出宛如玻璃破碎的爆裂聲,隨後聲響宏亮地落下,擊打我下方的防波堤……我想起俄國某位已故的大將軍,他曾訓練一支宛如怒海的軍隊,那刀劍宛如浪濤,吶喊聲也連綿不絕……這時的海邊幾乎沒有風,但某處此刻必定正值狂風暴雨;拍打上來的浪也持續增高。海浪的動作相當迷人,複雜得難以言喻,而且永遠有不同樣貌!有誰能完整描述這短短五分鐘的浪濤嗎?沒有人會看到完全相同的拍岸海浪。
或許在看過海浪捲起,或聽過浪濤震耳聲音後,沒有人會感受不到當中的莊嚴、肅穆。我曾注意到,就連馬或牛這樣的動物,在大海面前也會開始沉思。牠們駐足、凝視、聆聽,彷彿如此強烈的眼見耳聞,讓牠們忘記了除此之外的世界。
有一句和海有關的諺語:「海有魂也有耳。」這句話可以這麼解釋:如果你在大海面前感到畏懼,切莫洩漏你害怕的情緒;如果你吐露恐懼,浪濤將會瞬間拔高。這個想像對我來說如今似乎再自然不過。我得承認,無論人在海中或船上,我都無法完全說服自己相信大海並非生物——大海擁有意識和敵意。目前沒有任何理由能否定這個想像。為了要能將大海想成只是一池水,我得和它拉開一定的高度,才能將最洶湧的怒濤狂浪看作癱軟的泡沫漣漪。
但在夜裡,這原始的想像竟比白日時還高漲。夜裡浪上燐光的悶燃和閃光,看起來如此生動!那霜冷火光色調的細微變化,看起來多像變色龍!潛進如此的夜海,在藍黑色的黝暗中睜開雙眼,觀察追隨你每個動作的詭異光流;每一道穿透海流的光點,都像眨闔的眼睛!在如此時分,我們彷彿被某種恐怖的感受包圍,漂浮在某種生命物質裡,而其中的感受、所見與意志,都和無垠、冰寒、柔軟的「靈」相近。
四、
我徹夜未眠,聽著巨浪拍打上岸的漫天震響。但比這震耳欲聾的聲響和怒潮突擊而來更顯深沉的,卻是遠方海浪的低音。那像是無止盡的呢喃,震得建築直晃動,又像是無數騎兵的踏步和無數大砲群聚的響聲,一支從日升之處疾行而來、大如天地的軍隊。
我繼而發現,自己竟回想起兒時聽見海潮聲時那種模糊的驚怖感。即使多年後的今天,我在世界各地不同海岸聽到的海潮聲,依然會喚醒我兒時的情緒。的確,這情緒比我還要老上幾千萬個世紀,那是一種承繼自遠祖的恐懼總和。但現在我明白了,對於大海的恐懼感,不過意味著濤聲喚醒的諸多畏懼的其中之一。因為當我聆聽那駿河海岸的怒濤時,幾乎能分辨出當中每一種人類所知的恐懼之聲:不只是戰場上的巨大聲響,例如數不清的槍聲、無止盡的衝鋒,還包括野獸的吼叫、火焰燃燒的爆裂聲、地震時的轟隆聲、建築倒塌時的巨大聲響,以及較之更甚、宛如尖叫及壓抑聲般的持續喧鬧,那正是溺水亡者的聲音。那是最可怕的吵鬧聲,結合了所有想像得到的憤怒、毀滅和絕望的回音。
我告訴自己:海潮聲會讓人嚴肅,這難道不令人讚嘆?所有在更加浩瀚的靈魂經驗之海當中泅泳的遠古恐懼,都要與浪濤多樣的聲音和諧唱和。深淵就與深淵響應。可見的深淵呼應著無可見的前人深淵,我們的靈魂便造就自前人生生不息的滔滔洪流。因此,古老信仰所言的「大海怒濤即是亡者之言」,這背後必有更深的含意。亡者的恐懼及痛苦,的確藉由怒濤喚醒的深沉、模糊的敬畏之心,傳達給了我們。
不過,有些聲音比海潮聲更較人感動,而且是以更奇特的方式。那聲音有時也讓我們嚴肅以待,非常嚴肅。那就是音樂。
偉大的音樂是一場心靈風暴,翻攪著在我們內心難以想像的深處那些過往的謎。音樂或許也可說是一種神奇魔法,每種不同的樂器及嗓音,都能呼喚出數百萬不同的前世記憶。有能召喚出年輕、歡愉及哀憐之魂的聲音,也有能召喚出消逝熱情的苦痛魅影的曲調,以及召喚所有威嚴、偉大及輝煌情感幽靈的音符;這些全是消逝的狂喜,已遭遺忘的寬恕。對一個自認自己的生命不過始自百年內的人來說,音樂的影響似乎難以理解。然而,任何人若能發現自我的本質比太陽更為古老,心中過往的謎將迎刃而解。他發現音樂是一種通靈術,他會感受到旋律的每道漣漪,和聲的每股浪濤;某些無數古老的苦與樂的漩渦此時便超脫「生死之海」,在他的內心應答,讓他悟出道理。
苦與樂,總是在偉大的音樂中結合,因此音樂可比海潮聲或任何聲音更教人感動。但就音樂更廣的表達來看,悲傷總有弦外之音,那正是「靈魂之海」的波浪低語……難以想像人腦在進化出音樂感之前,體驗到的苦樂總和有多麼龐大。
曾從某處聽說,人的生命就是神的音樂——有歡笑、有淚水,有唱頌、有呼喚、有祝禱,也有愉悅及絕望的吶喊;這些絕不會從不死不滅者傳出,這些自成完美旋律。因此諸神不會要求加快描述苦痛音符的速度,如此會毀掉這首音樂!若沒有苦悶音符的組合,上帝之耳只會聽見難以忍受的噪音。
既然音樂的狂喜不過是過去無數累世苦與樂透過生生不息的記憶的總和,我們只有一種方法可以自比為神。所有累世的喜樂與傷悲都以無數形式的旋律及和聲,回頭糾纏我們。即便如此,百萬年後或許人間已不見日光,但我們此生的喜樂與哀傷,將會透過更豐富的音樂,傳遞至其他人心中,在某個神祕時分,揚起某些刻骨銘心的激情之苦。
試閱(二):〈碎片〉
他們在日落時分抵達山腳。那裡杳無人跡,沒有漣漪、沒有樹影、亦不見飛鳥,只有從荒蕪中浮現的荒蕪,而峰頂遠在天邊。
佛陀隨後與他的年輕僧人說道:「你所求見的將會示現在你面前,但目標遙遠,路途崎嶇。跟上吧,莫驚慌,你會獲得勇氣。」
登山時,暮色讓他們沮喪。那裡沒有人徑、不見足印。這條路落在一堆堆無止盡的崩塌碎石上,碎石隨著踏下的腳步滾動、翻轉,有時喀嗒喀嗒地伴隨空洞的回音滾落,有時踩過的東西會如空殼般爆裂……群星閃爍,黑夜深沉。
「莫驚慌,孩子,」佛陀如此教誨,「此地並無危險,唯路途滿布荊棘。」
他們在星空下登山——快,快——藉著超人力量往上爬。穿過高空迷霧後,他們看見腳下是一片比沿途更寬廣的景象,一片深不可測、宛如乳白浪濤的雲海。
他們毫不停歇地攀登,那輪廓無可見的東西在他們腳下悶聲地裂開,森森鬼火在每次碎裂中忽暗忽明。
年輕朝聖者的手擱在某個平滑的東西上,但那不是石頭;他拿起這東西,隱約瞧見一顆骷髏。
「別耽擱,孩子!」導師催促著,「峰頂仍在遠處!」
他們穿過黑暗朝上爬,一直感覺到腳下那悶聲的碎裂,看見鬼火忽明忽暗,直到夜色漸明,眾星落下,旭日即將東升。
但他們仍持續上山——快,快——藉著超人力量往上爬,周遭冰寒刺骨,盡是無聲闃寂。此時,東方燃起金色光芒。
年輕朝聖者眼中最先見到的是一片光禿的峭壁,他不停發抖,感到一陣恐懼。因為那裡不見任何土地,無論身前身後,四處皆無,只有成堆滿布的無數恐怖骷髏、碎骨和骨灰,而且處處散布著殘落人齒,宛如潮汐沖上岸的貝殼碎片,微微閃爍。
「莫驚慌,孩子!」佛陀大叫,「唯有強大的意志方能征服這片景象!」
在他們身後,世界已然湮滅,僅剩下方的雲海和頂上的天空,以及兩者之間的骷髏坡,斜聳直至眼界盡處。
旭日隨著他們緩緩升起,但陽光中沒有溫暖,而是冷冽如劍的凍寒。對驚人高度的恐懼、對無底深谷的夢魘,還有對空寂的驚駭,逐漸擴大,加諸在這朝聖者身上,讓他舉步維艱,所有氣力瞬間離他遠去,讓他宛如夢間囈語般呢喃著。
「快,快,孩子!」佛陀喊著,「時間無多,路途仍遠。」
但朝聖者大叫:「我好怕!而且我已經沒有氣力了!」
「力氣會恢復,孩子,」佛陀如此答覆,「且看看你腳下、眼前、四周,告訴我你見到什麼。」
「我辦不到,」朝聖者緊繃地發抖大喊。「我不敢往下看!我身後及眼前只見人骨滿布。」
「孩子,你還沒,」佛陀溫柔地笑道,「你還沒明白這座山是什麼構成的。」
他發抖地回應:「我好怕!非常怕!這裡只有人骨!」
「這是骷髏山,」佛陀回答,「不過,孩子你要知道,這些人骨都是你自己的!每個骨骸過去都曾是你夢想、幻象及欲望的巢窩。這當中沒有一個是別人的骸骨。全部,無一例外,這些全都是你無數前世的骨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