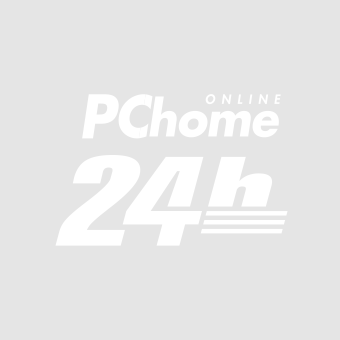商品詳情
內文簡介
<內容簡介>
在這裡,我們一起聽見真實的人、真實的故事
范琪斐30多年採訪生涯以來,最喜愛的作品
《說故事的人》入圍2021年《卓越新聞獎》Podcast新聞節目獎,
創造70 萬次收聽,2022年第一季編輯成書,圖文並茂,
收錄30張插畫與近50張照片,13組人物故事躍然紙上。
在這塊土地上,我們怎麼生活、怎麼思考、經歷了什麼?這些面向的問題,《說故事的人》在不同的受訪者身上感受到解答。《說故事的人》第一季編輯成書,講了十三組不同的人、不同立場的故事,讓有著精采故事、不被一般主流媒體青睞的人,有說出自己故事的管道。
這些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故事,不希望讀者用理性來「判斷是非」,而是期待用心細細「體會」,不同人面對不同的人生,選擇了什麼樣的抉擇與立場。
也許你會說這是別人的「故事」,但許多個故事串起來,這就是屬於「我們的故事」,用理解取代劃分你我,每個人的故事,都可能是你的故事!我們當代的故事,它不一定像童話有套路,卻無比真實。
「她的提問循序漸進,看似無招,卻都溫柔地正中要害。」──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接受愛的人,同時也可能是受傷害的人。
這些說故事的人,往往回不了真正的家,總是在療傷的路上。
第一個故事,疫情下的人,有的人關在家,親朋好友都不在身邊,家給人的親密感,被重新定義;有的人住加護病房,家人不願意隔離入院照顧長者,只剩下外籍幫傭願意。
第二個故事,全球化流動之下,外籍幫傭不僅照顧老人,也照顧小孩,然而時間一到便要離開,多年來小孩已把她認作第二個媽媽,這份分離焦慮影響了此後成長的人生。
第三個故事,台灣早年家庭之中小孩成員眾多,很多社經地位不佳的家庭會把孩子送出去當養子養女,孩子來回在寄養家庭與原生家庭之間,兩邊的爸媽可能把他忘掉了,但他從未忘記。
第四個故事,遇到不負責任的父輩,甚至讓自己成為乞丐,孩子對家長的尊敬與失落,如何幻化成為他自己成長的動力,他又如何看待這樣的家庭?
第五個故事,一個家裡,可能不只一個人受傷,因為家內性的侵害,可能受害者不只一個人,當傷害以愛為名,要如何走出來這樣的重重陰霾?
第六到第八個故事,從家的暴力,放大到國家的暴力,白色恐怖時期,不僅冤案頻傳,無法給予歷史正義,而受害者的心理創傷,還可能變相影響自己的下一代,這樣的歷史創傷與代間創傷,療傷之路該如何走下去?
第九個故事,國家暴力從台灣的故事轉往西藏,中共軍事統治鎮壓,許多藏人因為抗暴而流亡異鄉,面對跟原鄉親人的分離與重逢,台灣雖是他鄉,已是故鄉。
第十個故事,同樣是流離與逃亡,港人的際遇也不單純,書店老闆不願出賣名單給中共,在三根菸內的時間決定要挺身而出,將不義公諸於世,然後離港來台。
第十一和十二個故事,是關於捐贈精子與連結海內外血緣家族的奇特故事,一個身在紐約,卻子嗣成百滿天下的現象,重新定義了人們對於家庭與世界一家的想像。
最後一個故事,回到台北社子島的里長,他是卡在中間的人,卡在都市開發派與反拆遷派之間,這個故事專訪獲得卓越新聞獎提名,可以說是在地關懷與資本開發的辯證下,呼應著全書對於自身家園的愛與傷的重新理解。
新的故事,有待繼續述說,細細聆聽……
「平常有在聽《說故事的人》的朋友應該會感覺到,我們訪問了很多情感上有傷痛的人。我自己訪談的時候常常會哭,很多朋友也說,聽的時候,會跟著掉眼淚。其實《說故事的人》當初在設計的時候,並不是刻意找很悲情的故事,但常常是跟受訪者越談越深的時候,我們跟著他一起就走進了他心裡很柔軟的那一塊,這常常是他內心最脆弱的地方,但常常也讓我覺得是他最強壯的地方。」──范琪斐
無數個人是「數字」,單一個人則是「故事」。在新聞報導裡,事件中的「人」只是個數字,但當鏡頭聚焦在個人,我們會感受到這個人的悲喜、感受他面臨選擇的取捨,感受一個活生生的人,面對生命而成就自己的「故事」。我們說一個個人的故事,累積起來,就是我們當代的面貌,也是《說故事的人》最感動、也最想留下的價值,留下台灣當代的故事。當代人的故事,就是未來人的珍貴史料。
★本書特色:
三年多前范琪斐回到台灣,以她在美國三十多年的採訪經驗,籌組「說故事的人」影音團隊,一起探訪深藏在台灣的許多人的心事,專注傾聽、陪伴與療傷。這些故事隨著范琪斐循序漸進的提問,受訪者打開心房,往往傾訴的是最為內在的創傷。說故事的人誠摯,聽故事的人的耳朵也溫柔。十三組故事編輯成書,造就了台灣眾生相的面目,也別開生面地呈現台灣內在風景的多樣性:有在家庭裡接受愛同時受到傷害的孩子,也有國家暴力下的受害者。這些說故事的人,往往回不了真正的家,總是在療傷的路上。書中也有遠渡重洋來到台灣的新住民,重新述說自己在外地的故事,因而在這塊土地上,成為台灣這座溫柔島嶼的故事之一。
★名人推薦:
彭仁郁 專文推薦
王 師|牽猴子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創辦人
吳怡農|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李可心|美國台灣觀測站成員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唐綺陽|占星專家
敏 迪|國際新聞界的天之驕女
許芳宜|國際知名舞者
凱 莉|百靈果NEWS共同創辦人
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曾志豪|香港媒體人
楊貴智|法白站長、法客電台主持
詹怡宜|TVBS新聞台新聞部副總經理
鄒宗翰|同志人夫
蔡明亮|國際知名導演
謝哲青|作家、知名主持人
(依姓氏筆劃排序)
「讓別人說出藏在心裡最深處的故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聽過很多專訪,但只有范姊有這樣的魔力,勾出人與人之間最秘密的對話。《說故事的人》是台灣當代非常重要的聲音。它記錄了文化、衝突、人權與國族。用小人物的故事,照出一整個華人社會的影子。」──敏迪(國際新聞界的天之驕女)
「像個新聞界的搖滾樂手,30年來琪斐未曾停留在過去的美好,她超越自己的方法是透著更濃的人味,更貼近地表的真實,以其獨特的?事口吻,向我們投遞一個又一個屬於這個時代重要的故事,這樣的搖滾值得喝采和支持。」──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唯有真實的故事,才有帶動我們共同思考的強大動能。」──謝哲青(作家、知名主持人)
「琪斐近年來在國際新聞上的表現,是台灣新聞界最大的驚喜!有幸交會,更感覺到她的人格魅力,她是典型九宮人,有理想又聰慧,而且在自媒體時代,也能華麗轉身,巧妙跨界,滿足大家知的渴望。衷心向大家推薦《說故事的人》,除了好故事,還有好觀點,你不能錯過!」──唐綺陽(占星專家)
「在法國求學、工作、生活的八年多裡,除了書本,Radio France-France Culture(法國廣播公司文化頻道)可以說是我最重要的精神食糧。我回到台灣十多年,一直殷殷期盼台灣廣播界的文化土壤能長出足以滋養心靈,幫助我打開心靈複眼,看見生命多樣性的節目。在眾多podcast節目中異軍突起的《說故事的人》,幾乎像是我非常喜歡的兩個法國文化廣播節目“Les Pieds sur terre”(腳踏實地)和“A voix nue”(裸聲直說)的合體。期待學姊帶領的優質專業團隊能繼續發掘散布在台灣諸島,更多被掩蓋、忽視或遺落的生命故事。」──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目錄:
專文推薦 傾聽傷痛的溫柔空間/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前言
故事.1 疫情下的人
故事.2 我的第二個媽媽
故事.3 爸媽把我忘掉了
故事.4 我爸要我當乞丐
故事.5 受傷的人
故事.6 白色恐怖:誰的正義?
故事.7 白色恐怖:誰是受害者?
故事.8 白色恐怖:療傷之路
故事.9 回不了家的人
故事.10 逃亡的人
故事.11 我是捐精超人
故事.12 我的一千個兄弟姊妹
故事.13 卡在中間的人
<作者簡介>
范琪斐
資深媒體人,長期觀察台美兩地文化差異。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畢業,紐約大學媒體生態學碩士肄業。曾任中天、TVBS、三立駐美特派,寰宇新聞台《范琪斐的寰宇漫遊》主持人。長住美國紐約二十多年,2018年返回台灣定居。現為Line《范琪斐的TODAY看世界》國際新聞短評主持人。著有《買槍,養馬,呼大麻:范琪斐的美國時間》。2019年11月起為網路平台LINE TODAY上製作國際新聞節目《TODAY看世界》,並有網路節目《斐姨所思》談國際新聞,2021年錄製Podcast《說故事的人》節目,是由范琪斐、林瑞珠、陳彥豪共同策劃,范琪斐的美國時間與實在影像共同製作,百靈果News協同製作,本書《說故事的人,在療傷的路上》為第一季的內容集結。
★內文試閱:
故事.7 白色恐怖:誰是受害者?
英文有個說法,叫「collateral damage」,附帶傷害。這個用語最早是出現在六○年代的越戰,指的是美軍當時在打擊越共軍事行動,造成了許多平民傷亡。這些平民雖然不是目標,但還是死了;國際間就把他們稱為「附帶傷害」,後來這個用語被擴大使用,用來形容明明什麼都沒做,但只是因為運氣不好,就成了受害者的人。這次《說故事的人》要訪問的陳慧瑛,就是個附帶傷害。
她的父親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台大畢業,六○年代參與黨外的民主運動,三十二歲被被捕入獄,刑求逼供、判刑八年;他不服,認為憑自己的聰明才智一定可以贏得上訴,結果上訴之後加重刑期兩年,四十一歲出獄、結婚,生了陳慧瑛跟弟弟。
慧瑛六歲的時候父母就離婚了,父親不准她跟母親往來。從小慧瑛就覺得父親怪怪的,經常極度不安、疑心病很重;即使出獄多年了,仍然懷疑被監控,對親人也無法信任,每通電話都要錄音,對子女的生活也同樣嚴密監控。對小時候的慧瑛來說,爸爸把警總帶到家裡來了。
慧瑛三十歲出頭,說話輕輕柔柔的,有一點藝術家的氣質。她來到錄音室的時候有男朋友陪著,受訪者有人陪同是很尋常的事。我們通常會安排坐在錄音區外的沙發上,因為我們一訪常常好幾個小時,我怕陪同的人會坐不住;但慧瑛要求讓男友坐在她身邊,我有些意外,但也覺得沒什麼不可以。工作人員給兩位都倒了水,訪談便開始了。
{遭遇白色恐怖的菁英父親,出獄後罹患被害妄想、不再信任任何人}
范琪斐 妳覺得他跟一般的爸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妳同學的爸爸,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你小時候在看他的時候。
陳慧瑛 我覺得小時候最大的困惑應該是他沒有工作,因為他從就是離開我們老家、第一個老家,他就沒有再繼續工作了。那原本在那個老家,他是做碾米工廠,所以他就是老闆這樣,然後離開那裡之後,他就沒有要再找工作。他總是會說他在找工作,或是他要工作,或者是沒有人要他,或者是,沒有人看到他的才華,他明明就是台大畢業的這樣。他總是會唸著這些事,可是他還是不會去工作,還是沒有試著應徵這樣。所以最大的不一樣應該是在沒有工作這件事上。
范琪斐 他大部分時候都待在家裡?
陳慧瑛 對對對。
范琪斐 跟你們的相處時間應該很長啊?
陳慧瑛 很長,但是他不會真的在我們身邊陪我們啊!
范琪斐 他不跟你們說話的?就是不跟你們玩嗎?還是?
陳慧瑛 如果我們去吵他,或是去跟他講話,他可能就會說,我們這樣子吵他會害死全家。
范琪斐 我聽不大懂,為什麼吵他會害死全家?
陳慧瑛 因為我們家是,只要有人打電話進來,他就會錄音,他就會覺得某一些電話很重要,他可能代表了誰在監控他,或者是什麼狀況,然後他就會把它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從這一片錄音帶錄到另外一片錄音帶這樣;或者是一遍又一遍的,在他的訴狀上面劃重點,找資料、劃重點;或是看很多很多份報紙,看時事什麼,那些東西都對他來說都很重要,就是他在努力地洗刷他的冤屈。然後我不能打擾這件事情,那是他很重要的工作。
范琪斐 對他來講很重要。
陳慧瑛 對對對。他也會跟我們講,就是會跟我們講很多這個事情,可是我們當然都聽不懂。因為我是他第一個孩子,所以他基本上就是都會跟我說,然後會把一些證據或是一些資料攤在我身邊跟我說,這些事情是誰哪裡做錯事,法官哪裡沒看懂,或者是親戚怎麼樣,他都覺得我看得懂,或是我有看懂他的意思。我就是負責聽,可是我其實很不想聽這樣。
范琪斐 為什麼不想聽?
陳慧瑛 因為很累啊!就是總是在重複那一些他在意的事情,比如說誰偷了他印鑑,或是誰在哪一個細節上面偽造文書,或是誰在什麼時候做了什麼事情,大概就是重複這一些東西。嗯……,覺得他很痛苦。
比方說,他每天出門都要花很多時間鎖門;鎖各種東西,比如說房間的某一些櫃子,或者是某一些文件夾,他必須要重複地綁塑膠袋綁得很緊、把它放好,還有就是,晚上睡前會花一、兩個小時的時間鎖門窗跟瓦斯;然後,我們其實也都不能拿鑰匙,因為……就是我們沒辦法自己上下學,沒辦法出門玩,就是鑰匙都在他身上,所以我們沒有家裡的鑰匙,然後也不能出去。
范琪斐 OK,所以爸爸就管著那個鑰匙,也就是你們要出門,是要爸爸幫你開門?
陳慧瑛 可以這麼說,就是我們會一起行動,不太會分開;到國中開始要會自己去上學,就沒有再這樣。
范琪斐 妳有沒有問過他,為什麼不給妳們鑰匙?
陳慧瑛 我小時候應該有,但是結論應該還是一樣。就是他大概就會說:「這樣子不好,這樣不對,這樣會害死全家」什麼的,就是有人在看、有人在監視、然後有人在竊聽之類的,他就還是會這樣說。其實搞不好有啦!搞不好真的在我七、八歲之前搞不好真的有,因為那時候就還沒結束嘛!其實監控還是持續了一段時間,但是我那時候,就一直沒有理解這是什麼意思,所以我就只是,被我放在一種聽不懂他在講什麼的那個感覺。可能吧,可能是這樣。對,他給我釋放一種訊息就是外面很危險,反正就是很危險,就是不要問,就是很危險這樣。
范琪斐 所以妳們哪裡都不能去?
陳慧瑛 對對對。啊,我們也不能去畢業旅行也不能去,也不能去校外教學,都不行。
范琪斐 那到國中,妳現在比較大啦,那偶爾如果說出去跟同學玩晚一點可以嗎?
陳慧瑛 會被罵。
范琪斐 事先跟他講也不行嗎?
陳慧瑛 不行,事先就會更慘了。因為他就不會……就會跟你吵架。
范琪斐 他的理由是什麼?
陳慧瑛 他沒有很認真地在講一些理由,或是特別講什麼理由,但我可以看出他非常害怕。他很緊張、很害怕,然後會說我們這種行為都是要害了全家,一直到長大我當然知道,這跟他過去長期被監控有關嘛!還有他被抓的那個過程有關;但是在那個時候,我只是覺得,只是覺得他是一個嚴格的爸爸這樣,嚴格的大人。
{把獄中刑求的創傷,置換對孩子媽媽的抹黑}
爸爸非常的嚴格,姐弟倆也不能找媽媽訴苦;在慧瑛六歲的時候,兩人就離婚了。在爸爸的口中,媽媽是十惡不赦的壞人,所以不准他們跟媽媽聯絡。
陳慧瑛 他們在結婚、生孩子之後,爸爸其實有一些……顯露出一些就是被害妄想,覺得別人在我們的餐裡面下毒那一類的東西,然後就是,慢慢家裡的生意越來越差的時候,媽媽想要出去工作。對爸爸來說,這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就是他沒有成就。所以他就會很生氣地阻止媽媽,可是媽媽是一個從小就自己養活自己的人,所以她對這件事也很不諒解。所以我爸就開始羅織一些媽媽的罪狀說,這個是,她就是要來打我們、要來殺我們、要來害我們。她拿菜刀要來殺我們,她揍了爸爸什麼之類的。就會在我身上灌輸這些這些回憶,但我媽媽都說沒有這些事情。可是,我的確有一個印象是好像有被揍、有被打,然後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這樣。他大概會在我們身上灌輸這些事情,但是到了長大,但我現在回頭看……。
范琪斐 我再確定一下,所以這些事情有沒有發生?是你不記得,還是說?
陳慧瑛 我相信是沒有啦!就是比方說,他會說媽媽拿針刺我們下體啊!但是我小時候就覺得不可能,可是我腦袋裡面的確有這種印象,媽媽當然就說不可能,我幹嘛要做這件事?還有像是爸爸會說,媽媽有一次揍他,就跟他吵架的時候揍他的臉這樣,讓他就是整個牙齒都掉光。可是我也是小時候就覺得不太可能是這個樣子,怎麼可能這麼大力嘛?但是他的確有假牙,的確是滿口都是假牙。我後來回頭再去想,就是除了那個記憶可能是假的記憶以外,因為爸爸常常在講,可能就變成了一個真的記憶在腦袋裡;可是除了這樣以外,我覺得那些他說的那一些畫面,其實是刑求的畫面。
范琪斐 爸爸以前被刑求的畫面。
陳慧瑛 對啊!其實應該是他被刑求的畫面,只是他拿來講成,就是媽媽做的事情。到很後來長大之後,他有稍微跟我講一下刑求過程,大致上,就是很有名的那幾個刑求,包含就是,除了拳打腳踢的揍你以外,還有就是,去弄你的下體,可能是辣椒水去弄或是去揍他、或是去電他之類的,這些東西都是真的嘛!那我自己是覺得,應該是這個東西被他置換到我的記憶,就是他故意這樣說。
由於爸爸的一再禁止,慧瑛是一直到了高中才跟媽媽重新聯絡上;這是在一個熱心的老師鼓勵之下所做的嘗試。
陳慧瑛 在高中之前,我的確有一段時間,也是跟爸爸講的一樣,是相信她是個壞人;雖然半信半疑,但是好像不得不這麼想。然後爸爸那時候就是,那時候不准我們見面嘛,那媽媽就是每一次我們換學校,她都會保持跟老師保持聯繫,然後跟老師check我的狀況。她也會來看我們,然後也會寫信來,一直保持一種……讓我覺得說,萬一發生有什麼事情,我是有人可以找的這樣,因為那時候爸爸不跟任何親戚聯繫嘛!所以我的世界就只有爸爸跟弟弟。除了上課以外的時間,跟學校也是斷裂的嘛!所以就只有爸爸,所以就沒有跟媽媽聯繫,然後一直到長大,到高中的時候才跟她聯絡,是因為我繳不出班費。那個時候的導師就說,那妳要不要跟媽媽聯繫?因為反正你就跟她拿個錢啊,也不會怎麼樣,就大概從那個時候才開始正式跟她聯絡,然後的確媽媽就跟她的朋友有跟我見到面。我記得我就是很混亂,因為我就會覺得,我好像背叛了家裡,可是我又覺得這件事情……。
范琪斐 妳說的家裡,是指背叛了爸爸。
陳慧瑛 對,爸爸跟弟弟,可是我又覺得,這件事情它有那麼嚴重嗎?但是我有感覺得到,老師跟媽媽那個時候是有一種善意。可是我又很害怕,所以大概那一天有哭著罵媽媽,就是她來的時候,有跟她接觸到,有哭著罵她或是哭著說一些什麼,但是他們就跟我說回家之後,就不要跟爸爸說嘛!回家之後就不敢隱瞞,後來還是說了,說了之後就被罵,然後在那之後,就再也不敢跟媽媽有一些什麼接觸,就跟老師說,我不要再跟她見面。
人在青少年時期,因為荷爾蒙的變化吧?常常會有很多情緒的問題要處理,其中一個就是孤獨感。但在慧瑛的情況,這個孤獨感比一般人要嚴重許多。因為父親把她跟外界所有的關係幾乎都切斷了。唯一在身邊的父親,又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范琪斐 你開始是什麼時候覺得自己不大對勁?
陳慧瑛 國中會有一些傷害自己的行為,開始覺得自己好像怪怪的,但是沒有很明確。因為那時候只是覺得孤單跟憂鬱,但是還是有朋友。高中的時候,被排擠的時候比較明顯;就是那時候的感覺很強烈,就是有憂鬱、有焦慮、有憤怒這樣子。可是因為那時候媽媽有帶我去心靈成長團體,所以一切會有一個想像是,我如果再努力照顧自己,可能就可以好起來,然後大學進到人本去帶小孩之後,開始發現說有些疾病,因為他們覺得我想事情很跳,所以他們就開始懷疑我是不是……就我的朋友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ADD,就是注意力缺失這樣。我才開始覺得說,有可能有一些天生的東西在我腦中這樣子。嗯,那時候同時也在關注爸爸的腦部狀況,就是覺得他可能生病,那大概是什麼疾病啦!已經有開始在做功課,所以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也是有這樣子。大概是這樣慢慢開始覺得,應該要找醫生幫忙這樣子。
{大學後獨立生活,卻仍揹著父親的痛苦記憶}
慧瑛後來透過諮商,慢慢的想辦法自己療癒自己。她發現畫畫跟閱讀對她很有幫助,好像可以躲到另一個世界裡。到了上大學時,她想要搬離家裡,爸爸這一次居然同意了。說是她自己大學時自由自在的獨立生活,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時刻,希望慧瑛也能有這樣的經驗。於是慧瑛沒有再跟父親住在一起,就這樣過了十多年了。現在跟爸爸的關係,慧瑛自己認為還不錯,但回家見父親對慧瑛來講,仍是件非常辛苦的事。
陳慧瑛 其實我們一直都還不錯,從小都是這樣,只是我不喜歡被綁住。那長大之後,他沒有再綁我,那我也慢慢了解他的狀況之後,我們的關係也都很好。這是溝通上的部分,可是我沒辦法靠近他,就我沒有辦法回家,因為我會很難受,會沒有辦法呼吸,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回家,甚至回家看他都很痛苦這樣。就是所有的感覺都會……就很像是排山倒海地這樣淹沒我這樣,可是,你要真的說到底是怕什麼事情,或是什麼情況讓我很害怕?可能就是,過去累積了那麼多東西,他只要有一點點變化,他只要有一點點反應,我就會很難受。像前陣子我們一起出去玩的時候,我們一起在車上看著我們就是以前的老家。他就說:「那個不是我們家。」然後光是他這樣子講兩次重複的話,我就快受不了了,我就覺得:「你夠了,不要再講話了,就是為什麼一直都不相信我?」喔對,就是那種不被相信的感覺。還有就是,推他的輪 椅推出去,走在他覺得比較危險的地方的時候,他會很焦慮;他會用盡全身的力氣想要阻止我們再繼續推他。然後那個時候我也會覺得很生氣。大概是那種時刻的經驗,就是我看旁邊的人,就是我身邊那些一起出去玩的,他們都覺得還好,就慢慢跟他溝通,可是我已經受不了了。一點點事情就會讓我很不舒服,他一點點就是比較焦慮或是不安的反應,我都會很難受。
范琪斐 其實不容易了。因為我覺得妳其實也是被傷害的一個人,可是我覺得妳已經很去試圖理解妳爸爸了。就是從一個被傷害的人,我覺得爸爸其實算是傷害妳的人。
陳慧瑛 對啊!是。
范琪斐 妳去理解他這個事情,妳怎麼樣做到的?
陳慧瑛 嗯……,也許應該是說,我更希望的,不是只是去理解他,而是我可以比較分得清楚我跟他是兩個人。因為從小實在聽太多他的事情,我其實從小就是一個照顧者的角色,一直把他揹在身上,我們其實有點難分開。但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覺得我就會不知道我是誰,可是我現在漸漸地覺得,我應該要跟他……就是我應該要更清楚地分開我們兩個人,就我不是代替他去感覺罪惡,或是代替他去承受孤單,因為我有幫他承受了太多這個東西。所以對我來說,去理解他可能也是為了要釐清我承受的什麼東西是過多的,然後我要怎麼分開我們兩個人,讓我們兩個變成獨立的人這樣。
范琪斐 這個,最困難的地方在哪裡,就在這個過程裡面?
陳慧瑛 最困難的地方……我覺得,可能就是因為我一直都很沒有……從來沒有去區分過這件事情,所以到這幾年開始慢慢意識到,有些東西是屬於他的痛苦,我沒有辦法幫他承擔的時候,就是發現那些黏在一起的東西已經混淆了,就是從小我跟他被綁在一起,那個混合在一起的東西,已經沒有辦法清楚地區分,所以那個困難是,可能困難在於辨識它;辨識我們兩個之間,哪一些是屬於我的感受,哪一些是屬於他的人生。可是我一想到我要放掉他的人生,我就會覺得很難受,就是好像我就是說出,我跟你是不同人;你的人生是你的人生,然後你就是這麼、這麼悲傷的人生,我沒有辦法。我好像說出這樣的話的時候,就會讓我覺得我丟下他;好像是割掉身上的某一個部分,很痛,然後很殘忍,可是明明那就真的不是我。
范琪斐 現在還揹著嘛!我覺得你到現在還揹著嘛,那怎麼辦呢?
陳慧瑛 好像也不能怎麼辦,就是慢慢的,在每一次發生,跟他發生的一些事……,因為我覺得接下來他就是步入晚年,應該說他就在晚年裡,就是他會經歷各種身體上的,可能他會受苦,會有各種沒有辦法再控制,但他又想要在那個沒有辦法控制裡面,抓回一點控制的感覺。然後在這些他想要掌控,然後我知道他已經沒有辦法控制,然後我看著要跟他溝通他想要控制的部分。比方說,他堅持不做什麼治療的時候,我會不舒服,或是我會覺得為難之類的時候會遇到很多衝突;那個衝突的過程裡面,我就會一直不停地要再回到過去那種,很難受的情境跟那個害怕裡面。我也不曉得要怎麼說那種感覺,就是在那個過程裡面,因為情緒都在那個時候才會出來,就才會有機會去理清楚這樣,或是各種跟人的關係,或是工作上的事情也會遇到一些情緒,那個都會有關係嘛!就慢慢去理清楚。可是我也知道大概,就算爸爸今天離開這個世界,這還是會是我一個議題,搞不好就會一直到死為止,都會有這個議題。就像他們到死為止,可能都會必須要面對刑求,或者是監控帶來的那些害怕。我覺得那個東西,在死前的孤單,應該也是就像我要去承受那個感覺一樣。
我這時候才理解,為什麼慧瑛在接受訪問的時候,需要男友的陪伴。因為分享這樣的故事對慧瑛來講是件很辛苦的事。能不辛苦嗎?連我這個聽的人,都覺得好辛苦。(未完)